读《邓小平时代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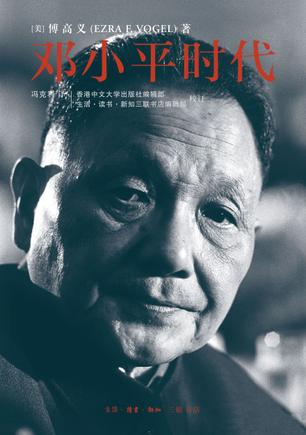
读完褚时健,就想找找类似的人物传记,于是我想到了他——邓小平。于是买了本《邓小平时代》。实体书,砸死人那种。
邓爷爷去世时,我六岁。关于他的记忆,马马虎虎。经常听说三起三落,经常听说黑猫白猫,经常听说画了一个圈,经常听说邓小平理论,却不知道为啥三起三落,为啥黑猫白猫,画圈干啥,理论又是啥。借这个机会好好脑补下这段历史。
这本书读了很长时间,断断续续。看见陌生人名,就去维基百科上搜(为啥不去国内百科,我想都应该懂得),总之查了好多资料,毕恭毕敬,像个学生一样,划线批注。
像这样的书,大陆版本,肯定是阉割过的。据说《邓小平时代》大陆版去掉了5.3万字(请参考http://cn.nytimes.com/china/20130321/cc21dengcompare/ )。
关于这篇文章,不会去论述政治上的事件(该听说的应该都有所耳闻,不该知道的,你得翻墙或者是读一些书才能捕获到,如果你想了解新中国历史,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。历史教科书上没有的这里面多少都会介绍几句),我会摘抄一些书里面描述生活里小平爷爷的片段,让我们去感受下伟人普通人的一面。

1930年初,邓小平再次回到上海汇报工作,期间去了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,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。医院的条件很差,她在生产时染上了产褥热,几天后便去世了,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。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,但他立刻回到红七军继续工作。在这惨痛的一年间,后来又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,与沪上一位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(金维映)产生了感情。
和毛泽东一样,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,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向对手发起挑战。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(一名福建籍干部)的失败主义政策,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。在后来所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”第一落”中,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籍一职,并和3个同事(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、谢唯俊和古柏)一起受到了严厉批评,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。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,被称为”毛派头子”,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他的行列,和他离婚,嫁给了批他的人之一、在法国时就和邓相识的李维汉。幸运的是,邓小平的另一位在法国时的故交、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,在他下放几个月后把他叫回来,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。
据邓榕说,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——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、自己在党内收到严厉批评和责难、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——之前,邓小平的朋友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、爱说爱笑的人。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剧和挫折后,他变得更为内敛,少言寡语。

1969年10月22日,邓小平与妻子卓琳、继母夏伯根一起,离开了他们居住了10年的中南海。一架专机把他们送到江西南昌,邓小平要在那里参加劳动,接收毛泽东思想再教育。他们获准携带一些个人物品和几箱书。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,但未得到批准。不过,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,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信转交毛泽东。邓小平登上飞机时,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待多久。
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,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,但据女儿邓榕说,父亲其实是一个有感情的人。她说,父亲在北京挨批的3年里身体消瘦,面容憔悴,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,恢复了健康。他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,”文革”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。但是1970年1月1日,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,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。邓榕说,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,围着小楼转40圈。用她的话说,邓小平”一圈一圈地走着,走得很快,…..一边走着,一边思索,……一步一步、一圈一圈的走着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”。他将在北京重新担当重要角色的前景,是他的思考有了目标感。邓小平从来不跟妻子儿女谈论高层的事,但是妻子和女儿邓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,又了解北京的政坛,所以能够觉察到他的心情和关切。据邓榕说,他们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得到前途和中国的未来,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。
1968年,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,结果摔断了脊椎。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,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,结果导致病情恶化。后来他获准转到北医三院,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,胸骨多处骨折,而且发着高烧。邓朴方在医院里昏迷了3天。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,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,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,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。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校医院,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。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。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,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。据邓榕说,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,卓琳哭了三天三夜,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,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
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,为了避免生褥疮,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。邓小平在邓榕、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,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。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。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提到”文革”时,邓小平情绪激动的称之为一场灾难。
在江西安家之后,邓小平和卓琳每天6点半起床。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,在江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,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。然后他根卓琳一起,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,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。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,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。
吃过早饭后,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制造厂,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。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,很像50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。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,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,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。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份,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”老邓”就行,这是中国人对年长同事的常见称呼,邓小平干活时,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的生活外,不跟工人谈论任何别的事情。
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和料理家务。午饭后,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,然后阅读他们带来的书,有中国历史典籍和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之类的小说,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。当时还没有电视,但是他们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。他们晚上10点上床,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,然后睡觉。孩子们的陆续到来,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。邓朴方在1971年夏天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,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。
除了在工厂劳动,邓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,邓小平也在家里帮着擦地劈柴。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比过去要少,因此日子过得很节俭。夏伯根养了一些鸡,使他们仍然能吃上鸡蛋和肉。邓小平减少了吸烟的数量,几天才抽一包烟。他上午在工厂里不吸烟,只有下午和晚上抽几支。他也不再喝红酒,只在午饭时喝一杯便宜的当地酒。长女邓林和次女邓楠仍能从工作单位领到一点工资,他们来后便和没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这点钱。
“文革”对国家、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。但是,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在一起的邓榕说:”他没有意气用事,没有情绪消沉,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。”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,譬如1949年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、1958年至1972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。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、淮海战役的同事,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,情绪低落。

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9天以后,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唐山发生大地震,官方统计有24.2万人死亡。北京也有强烈震感,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结构受损。如同帝制时代一样,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征兆。邓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,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,一直住到他们不再担心房子倒塌。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之后,从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复工作,他在宽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3年一样,又变成了以家人为中心,并只能从报纸和电台上了解新闻。
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。他8点用早餐,9点到办公室。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,包括大约15份报纸,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、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、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。为了解最新动向,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。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。文件在上午10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,他当天就会批复。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片纸,那里总是干净整洁。
在上午3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,邓小平很少会客,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。在家用过午饭后,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,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。如有重要外宾来访,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,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。
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,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,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:制定长期战略;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;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;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。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,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,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,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,最后由他拍板。在另一些问题上,例如国防,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,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他在亲自制定战略时需要知道的情况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。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,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议。他的大多数电话都由王瑞林处理。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别人口头通报情况,虽然部下们希望他对来访者的最新活动有所了解。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,邓小平通常会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,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,和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。他关注新闻,对体育也有兴趣,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。但是他与牌友、甚至与家人都不怎么闲聊。邓小平有”不爱说话”的名声,即便在家里。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,而会见外人时,人们则看到他机警,活泼,甚至强烈。
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,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笔记,而能讲的条理分明。通常他唯一的笔记就是他讲话的主题以及他所要诉诸的人群。1985年过了80岁以后,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写、编辑和陈述的长篇讲话。除了1992年南方谈话等少数例外,他的讲话不再被加工成有标志意义的长篇文件。
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、言谈风趣,但在家人之外,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。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,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。他们知道,在紧要关头,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,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。实际上,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,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,视其是否有用。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,他以此清楚的表明,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,而不是任何地域、派别或朋友。他既不心机复杂,也不怀恨报复,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。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、急切、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,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。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,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。作为最高领导人,邓小平行为一贯,统治方式始终如一。
伟人也有他普通人的一面,生活给予我们太多改变,我们都需要一颗勇敢的心。